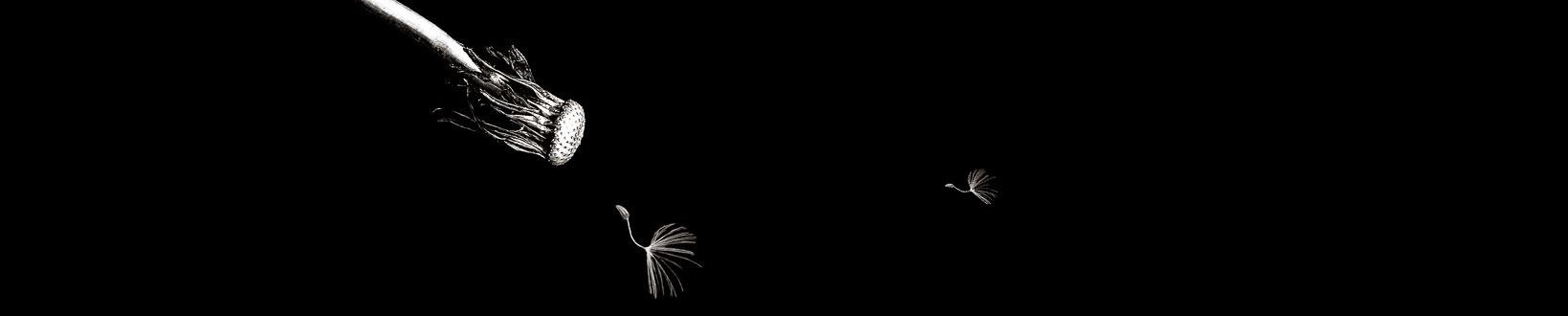铸梦感言 | 编剧高金勇:黄土高原的黄
陕西,对一个山东男人而言,有着令我自己惊讶的情结。
长安城,咸阳城,终南山,白鹿原,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这些名字一直在我血液中流淌,以至于我的笔名杨关三,也是取自《阳关三叠》,至今已经用了整整十年,而与这支曲牌对应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的情景,正是发生在长安城外一处酒肆的二楼临窗的位置。
黄土坡,延安,窑洞,鲁艺……对我而言,完全不像长安那般与生俱来的熟悉。当飞机掠过华北平原,向西刹那间驶入太行山脉时,我从机窗往下望去,千沟万壑,渺茫无边,我从未清晰的知道太行山以西竟是如此地理。我在想,生活在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上的同胞,是怎样度过了漫长的几千年,是怎样靠着双脚丈量着这莽莽群山。当太行山的葱翠变换为坡顶的黄色和坡上的黑色时,我知道,延安,离我越来越近了。几乎每一条坡间的山川之地,都挤满了在这里生生不息的族群;几乎每一座山坡的山脊之上,都有一条黄色的蜿蜒土路,通往坡顶,坡顶是为了生存而开垦出来的或大或小的一片平整的耕地。如果两千年前,我生活在这片土坡之上,我想我不会像愚公一样移山,而是带着族群,跋山涉水,去往一个富庶之地。可是,这里的人们,却在这片土地上固执的繁衍生息着,我很想飞机马上落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甘于忍受这里的贫瘠和困苦。

飞机落地后,去往延安大学的路上,我没找到答案。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地貌实在是太过逼仄和狭促,即便是住进了像极了窑洞的宾馆,我对这里的态度仍旧没有太多改观。直到接下来的几天,去了杨家岭,去了梁家河,去了安塞和延川……我双脚踏在舒服的黄土地上,看着塬上丛丛亮绿色的低矮灌木,嫩绿色的白杨,还有不时的在绿色中间杂而生的梨树开满了的白色的花,色彩错落而有层次,叠翠纷繁。我一直不明白关中派的作家缘何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无尽的热情去讴歌生养自己的这片贫瘠之地,现在我明白了。若是我生养在此,我也会如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一样,哪儿也不去,脚踏这片土地,心里才踏实。“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可以作为注脚,为八十年前鲁艺的那群风华绝代的年轻人,为八十年后心心念念仰慕而来的我们这群人。
感谢研修院特意安排去了路遥故居,2015年秋天的时候我特地去了蓝田白鹿原,去瞻拜了陈忠实先生的旧居。庆幸的是,那里还没成为游人如织的观光景点,但拆建正在进行。不成想第二年的春天,先生便去了,旧居自此变成了故居,如同路遥先生的一样。陈忠实先生动笔写《白鹿原》之前,回到白鹿原老宅,据说是住了五年,终于写完了这本“死后能枕在棺材里”的伟大的小说。同样的,贾平凹每次创作,也是把自己隔绝在旷无人迹的一处野外小屋,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无独有偶,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又何尝不是饮冰而作。只有回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上,心里才觉得踏实,笔下才有文字流淌,哪怕这片土地仍旧贫瘠荒凉,在他们心里,却始终是丰饶不可方物的。每一个用心创作的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心灵原乡,这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魂,是他们的来处,也是归途。如同贾樟柯电影中的临汾,如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失去了原乡,离开了原乡,他们便不再是自己,找不到自己了。
作者 | 高金勇
编辑 | 教学科研处 杨宗哲